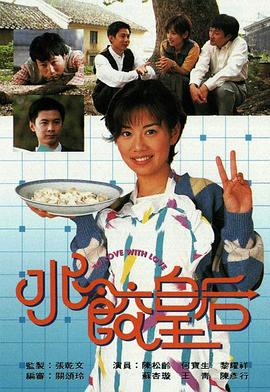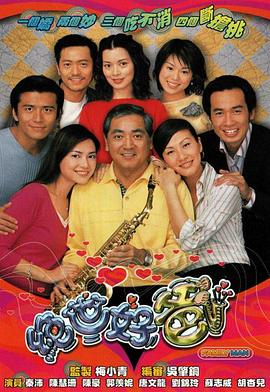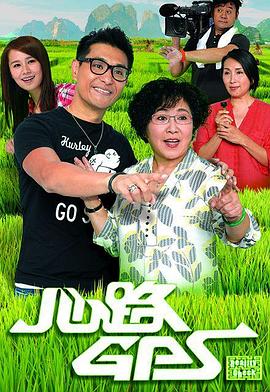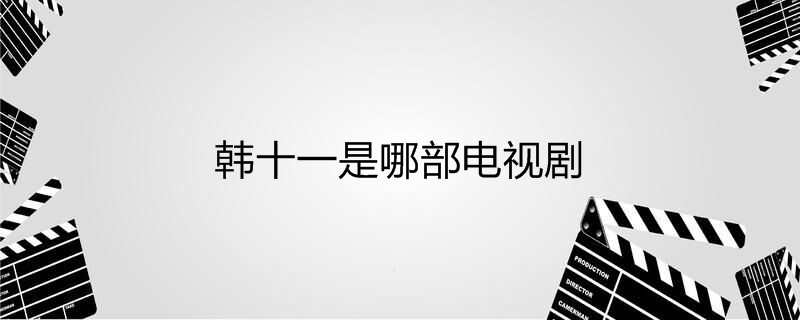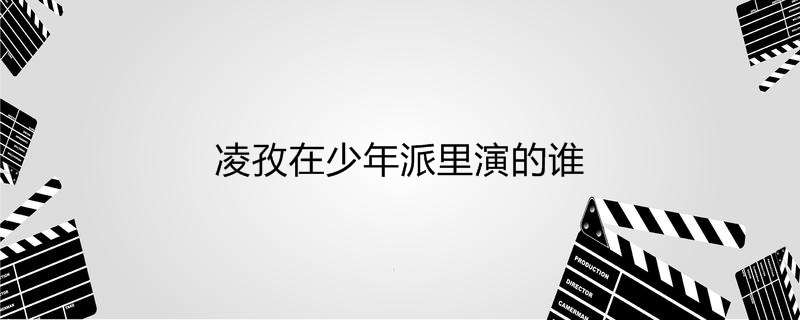引子:一记警钟——当精英开始反叛社会,试图医治又或者绝处自焚,怎能纷歧声叹息。
由邱礼涛导演的电影《拆弹专家2》于2020年的最后一个周末走上大荧幕,影片聚焦于拆弹专家潘乘风这一人物,在以香港九龙国际机场爆炸这一未发生事务的华丽预设画面后,引出了五年前潘乘风的工作经历及后续生活。

导演注重于潘乘风主观感知的呈现,出现多次“主观的真实”段落,且主角在被装配假肢后又进行了一次记忆植入,使影片差别于之前港片的拳拳到肉,反而增添了超脱现实之感,具有后人类时代“人机合一”的赛博格奇观。

1、 主观视角限定的情绪控制
从业三十余年的邱礼涛在香港这片电影的沃土中虽不是遮天蔽日的大树,但一向是剑走偏锋的叛逆者,从奠定“香港cult片之王”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到《爱情梦幻号》,再到《花田喜事2010》,直至本日看到的《拆弹专家》系列,邱礼涛涉足过商业电影的多个分支又不拘泥于一个类型,近八十部指导作品背后是对观众观影心理的强大认知。充分的观众认知后导演玩起了情绪控制(或者说情绪引导),这在《拆弹专家2》中是习以为常的。

例如,影片中潘乘风失去左腿而后进行高强度的身体训练、超标准的体能表现后仍不得录用时,对朋友董卓文的偏激控诉,导演在这一段落中把观众高度控制在了潘乘风的主观感受中——辛苦训练富有成果的场景镜头快速剪接后接下级领导毋庸置疑的拒绝,导演涓滴不给观众喘息和思考的余地,使此时的观者已被完全代入潘乘风的小我感受,这个“用完即弃”的社会对潘乘风这样的专家都如是残忍,暴怒与情绪扭转在此时逐渐显现。

导演故意忽略了身为残障人士确实无法胜任拆弹专家这一职业,完全站在潘乘风小我心理这边,带着观众一同坠入魔道。这无疑是导演完备预判下操纵心理的结果,这样的叙事方式完全符合特吕弗在谈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所说的“要把观众拉进情境中,只需要把动作分解成细节,然后从一个细节到另一个细节,从而使每一个细节都轮流强迫观众注意,让观众感受到人物所感受到的,”而“细节+细节”这一剪辑序列也常常具有建立观众心理情景、强化心理感应的作用,这在悬疑片中是经常用到的方法。

2、 赛博格意味的人物设计
在类型片的探索上我们同样看得到导演的野心,《拆弹专家2》定义为动作、犯罪类型电影,但导演始终尝试用穿插叙事的方式完成剧作悬念的搭构,且开篇就炸断主角腿部以构成“装了假肢的英雄”这一类科幻片的人物设定。

影片前期毫无遮掩地拍摄了潘乘风第一次佩戴假肢的过程,画面的典礼感为角色注入了一缕“非人”的色彩,这样的设计才让以后出现一群警察追不上佩戴假肢的残障人士的场景时显得能够站定脚跟。不但如此,影片还使用了“植入记忆”这一现实主义看来十分戏剧化的处理来为潘乘风的第二次转变打下基础,这将以往香港犯罪片中《无间道》似的人物内心心理矛盾转变为一场“精神突变”,再次扭转不再是拆弹专家潘乘风的小我想法,而是被动失忆后出现的另一个潘乘风。

但是影片在这一点上未曾深入描述,仅在医生寥寥几句失忆可能会导致性情大变的可能性中完成解释。但这样通过科学手段致使人物“精神突变”再次为潘乘风带来一丝类赛博格的被设定的意味,导演浅尝辄止地利用科技完成了犯罪动作电影中的赛博格奇观。

3、 亦正亦邪的英雄
与多数犯罪类型片拥有一正一邪的冲突较量差别的是,《拆弹专家2》中正与邪都成为了潘乘风这一英雄人物的一部分——零失误、待人和善的拆弹专家是他,狂躁易怒、建立反社会组织“复生会”的也是他,整部影片的最大反转来自于潘乘风的转变。

这样的英雄设定打破了观众的观影期待,又重新建构了这套体系,导演邱礼涛在电影正常上映的前提下借疯魔英雄之口触及了这一“病态社会”——让观者看到潘乘风努力复健、按时吃药仍不得复职,药物副作用与内心煎熬的双重折磨下,角色走向极端,在表彰会上拉出的黑条幅“用完即弃”四个大字深深震慑着观众,疯魔后的潘乘风喊出了生为人本该释放的愤怒和为自己力排众议的态度。

导演将英雄置于非常态化才说口出此言,但这番话也是导演对社会的反叛与控诉,而愤怒该如何消解呢?影片又十分“及时”地送上“植入记忆”这则良药,实际上是对“病态社会”的一种解构,如果连记忆都可以任意置换,人生在世又有甚么意义呢。但导演并未将重心置于此处的讨论,随着记忆的植入潘乘风很快找回了那个“拆弹专家潘乘风”,继续了英雄献身拯救世界的神话。这种“正邪同体”的英雄设计,重建了英雄模式并愈发与现实主义割裂。

影片非论从剧作结构还是视听语言上都有着可圈可点的表现,使人惊喜的是潘乘风这一角色的塑造,疯魔的表象背后是愈发具有人味的英雄设定,而我们人人也有了与英雄更近的距离。当精英开始反叛社会,试图医治又或者绝处自焚,怎能纷歧声叹息,《拆弹专家2》为我们敲了一记警钟。

一影一话 谱人生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 书字可抵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
终南影话 电影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