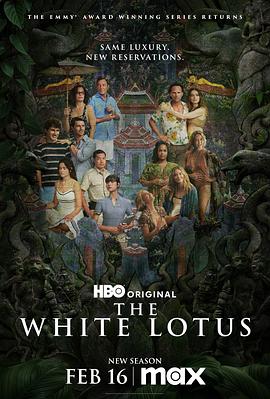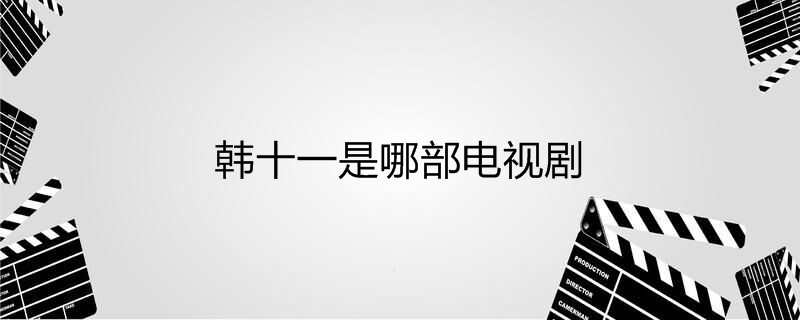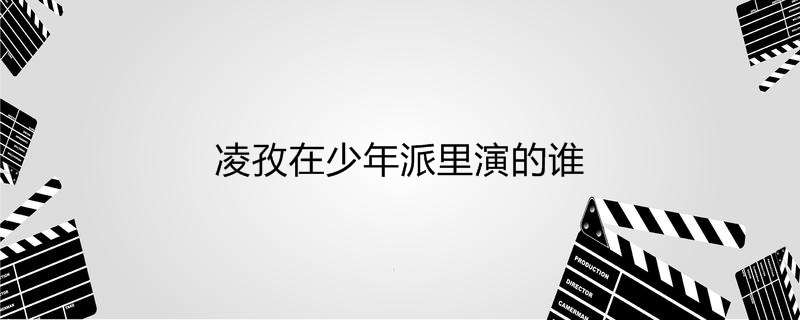采访 | 郝琪 郝继
文 | 郝琪
编辑 | 露冷
7月16日午时,一条被等待了很久的消息终于传来——电影局发布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全国影院将从7月20日开始,有序恢复营业。这意味着停工178天的内地影院,即将重新开门迎客。
与想象中的兴奋相比,许多从业者对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平静,外加将信将疑。比如刘建峰。他所在的影院在一个常住生齿80万的县级市,60个厅、720个座位。得知消息时,他正在出租屋里睡觉。微信上,老板发了张电影局的通知截图,平静地告诉他可以复工了。

摆在刘建峰面前的是一摊亟待收拾的混乱场面。影院要开业了,要把几个回老家的人叫回来,要请广告公司做防疫宣传标语,要在地上贴好间隔线,在各个位置贴上购票二维码,要购买消毒物资,还要重新盘点货品,把过期的扔了,催经销商赶紧上新货。 “总之一个字, 乱。”刘建峰告诉《贵圈》,照现在的进度,20日肯定开不了业。这两天又赶上周末,相关部门也不上班,各种资料都无法送审,25日能开业不错了。
7月17日17点40分,成都和平电影院售出影院复工后全国第一张电影票——《哪吒之魔童降世》。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该影城放出20日的165张票,当晚全部售完。尽管影城当天全部收入仅为16.5元——网络售票每张3.1元,其中3元为售票平台收取的服务费,影院实收0.1元——但影院负责人还是为“观众没有抛弃我们”感到高兴。
这场未曾事前张扬的自发行动是人们这些天情绪的写照。无论是电影行业从业者,还是更多的喜欢电影的观众,大家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1
从6月起,刘建峰就很少出现在影院了。
疫情刚开始时,他还时常独守商场五楼的影院前台,告知偶然经过的人们影院暂停营业。6月,气温上升,也没人在影院附近逗留了。他每周去一次影院,到各个影厅将放映机打开空转一下。刚开始还能放片子,后来片子密钥也没了,就只能放广告,按下暂停键,晾一下昼,避免设备因长时间闲置而损坏。其余时间,刘建峰在家睡觉,用扑克牌叠纸盒、看短视频网站上的讨好型人格分析视频自我反省。
楼下商铺的人偶尔跑上来问他,影院何时开业。他总是回答:“快了快了。”他真是这么想的。4月他就预测过,影院大概会在7月恢复营业。理由很简单,“国家不行让影院的暑期档断了嘛”。他所在的影院,春节档占全年票房50%,暑期档占30%。这么大的份额要是没了,“那就真没几家影院扛得住了”。
后来疫情来来回回,影院甚么时候恢复营业这事,刘建峰自己也不太确定了。“快了”成为不知如何应答时保全面子的敷衍。复工日子一拖再拖,期待早就拖没了。影院不再进行日常维护,每个月20日前,他把七八个员工叫回来搞搞卫生。搞卫生是次要的,首要是确认这些人还没辞职,给大伙儿发点生活补贴。其他的,也就不再操心了。
复工的消息突如其来, 从接到通知到恢复营业只有不到两个工作日,多数影院来不及准备。《贵圈》联系了十几家已开票的影院,不少都表示忽然被通知开业,特别忙,没时间接受采访。
同样措手不及的,还有一首网络上热传的名为《我想陪你看电影》的歌曲——它表达了普通人对去影院看电影的期待,也将因疫情延期的电影片名都写进歌里。因为《通知》来得突然,制作方来不及邀请专业歌手演唱,干脆把demo版发了出来。
豆瓣“探访曾经常去的电影院”话题下,网友“某S”发布了自己制作的视频《我带上几张旧电影票根去了趟电影院》。视频拖拖拉拉做了一个多星期,她常想,“会不会在这过程当中电影院就开门了,我就不消做了”。7月15日,视频发上彀,第二天复工消息传来,她觉得自己像只报喜鸟。
2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也经历了这样的“突如其来”。 7月13日,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发出公开信,表示为解决复业后无新片上映、影院将面临更大经营压力的问题,决定“用自己最为珍视的作品——《第一次的离别》,力挺影院复业,为中国电影业的复苏贡献一份力量。”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讲述了新疆男孩艾萨和好友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对母亲感人至深的子爱之情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讲述了新疆男孩艾萨和好友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对母亲感人至深的子爱之情
公开信发出后,很快,上海联和电影院线、太平洋影城、星轶影城、四川峨影影业等知名院线和影管联系了出品方。三天后,复工消息不期而至。作为发行方的大象点映“狂捶键盘喜欲狂”,加班加点进行母盘制作、硬盘复制、秘钥制作,准备发行通知,联系最快的快递,将电影拷贝在7月20日前寄给各大影院。
去年3月30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水泥看过《第一次的离别》。映后交换活动上,他问主创是否会在内地公映。制片人告诉他,顺利的话会在暑假看到。他挺喜欢这部电影,特意找导演王丽娜要了签名。
如今发现它成了影院复工后的首部定档新片,水泥情绪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纯牺牲”的决定,这类文艺片注定在正常运作的院线市场中拿不到多少排片。但在眼下尚不明朗的境况中,此举是“赤诚的”,“对这个行业有真诚的愿望”。
水泥201726岁,在广东顺德生活,自称不及格影迷。票根显示,他日常看电影的场所,顺德与香港各占一半。在顺德,他常去的电影院在一栋独立建筑物的三层,人们观影的社交属性更浓烈,观影时扳谈是常有的事,为此,他没少在观影半途愤而离场。
疫情到来前,每个月至少一次,他从顺德出发,坐三小时大巴去香港。在油尖旺下车,那里有一家百老汇影城,他是会员。抵达通常在上午,油尖旺尚未苏醒,通往影院的900多米路,他最常遇到的是中年搬运工和长者,以及密集分布的24小时便利店。他会在百老汇看一整天电影,最多时一天五场,再搭19点30分最后一班大巴回顺德。
上一次看电影,他搭清晨的大巴车去了广州。那是1月18日,周六,电影《蕃薯浇米》,顺德的影院没有排片,离他最近的有排片的影院在广州,仅有一家影院上映一场,上午10点开始。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以后,有接近200天,他再也没有进入影院。
这是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感到莫衷一是的一段日子。7月初,北京影迷某S去望京吃冷面,顺道去常去的影院看了一眼,伸手在前台一摸,一层厚厚的灰。
后来她带上这些年攒下来的票根,去对应的电影院,拍下一支视频做纪念。她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影院大门紧闭,只有植被探出围墙;她去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发现影城招牌已被拆毁;多数影院保留着贺岁档的宣传物料,热闹的红色蒙了灰,她觉得时间凝固了,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裹足不前,“心里挺复杂、心酸的”。
 4月18日,停摆的山东某电影院,还保留着贺岁档的宣传物料(图源:视觉中国)
4月18日,停摆的山东某电影院,还保留着贺岁档的宣传物料(图源:视觉中国)
在MOMA百老汇影城,某S看到大厅的墙上写着“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部同名电影的宣传物料。但在当时,她觉得这句话真“衰”,“像被说中了一样,电影院关闭没有尽头。你根本不知道甚么时候能够回来,我在哪里,它在哪里等我。”
3
刘总经常怀念2002年的冬天。那年冬天,电影《英雄》上映,影院摩肩接踵,他们几个工作职员在影院忙了半个月没出门。那是她入行的第一年,很快,非典就来了。2019年,她从那家影院辞职,开始经营位于北京顺义区的那家影院,第二年,新冠疫情来袭,她感慨“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头两个月,刘总觉得,在家躺着就是为疫情作贡献。但躺的时间越长,负担就越来越重,她既焦急又麻木。三四月份,她一度以为影院要复工了,到了6月她又猜测,那么多地方病例清零,总该开业了。
在二线城市的电影院工作的吴妍珠发现,3月复工传言流出时,有影院申请了影盘,后来被叫停,只好又把盘寄了回去。她所在的影院没有参与那一拨申请。一度,她正常上班,与同事轮流值班,将各个影厅双方的大门打开通风。影厅漆黑一片,她一小我打着手电筒,只敢打开进场门,站在通道往里看,像电影《闪灵》中的场景。
 3月28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一家电影院仍处于闭门歇业的状态(图源:视觉中国)
3月28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一家电影院仍处于闭门歇业的状态(图源:视觉中国)
刚开始,她还编辑、发布影院的公众号文章。可5月开始,公司停发工资。她问总经理:“公众号还要发吗?”得到的回复是,“谁让你发,你就让谁给你发工资。”
一切陷入静止。直到7月16日消息传出,影迷群里像“鱼塘炸了”一样,重新恢复生机。也有人泼冷水,语重心长地奉劝众人切莫高兴得太早,多数影院不会在此时开门,因为缺少热门影片的拉动,开业就意味着赔本。但也有常来观影的观众力挺:“只要开门,不管放甚么,我必然会去看。”
刘建峰感动于观众的热情,他说影迷们对复工的兴奋,甚至比他们这些行业内的人都高——那天消息传来,他的反应是“哦”,观众们的反应是“哇”。